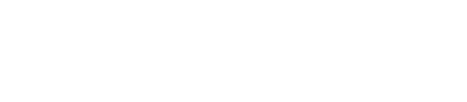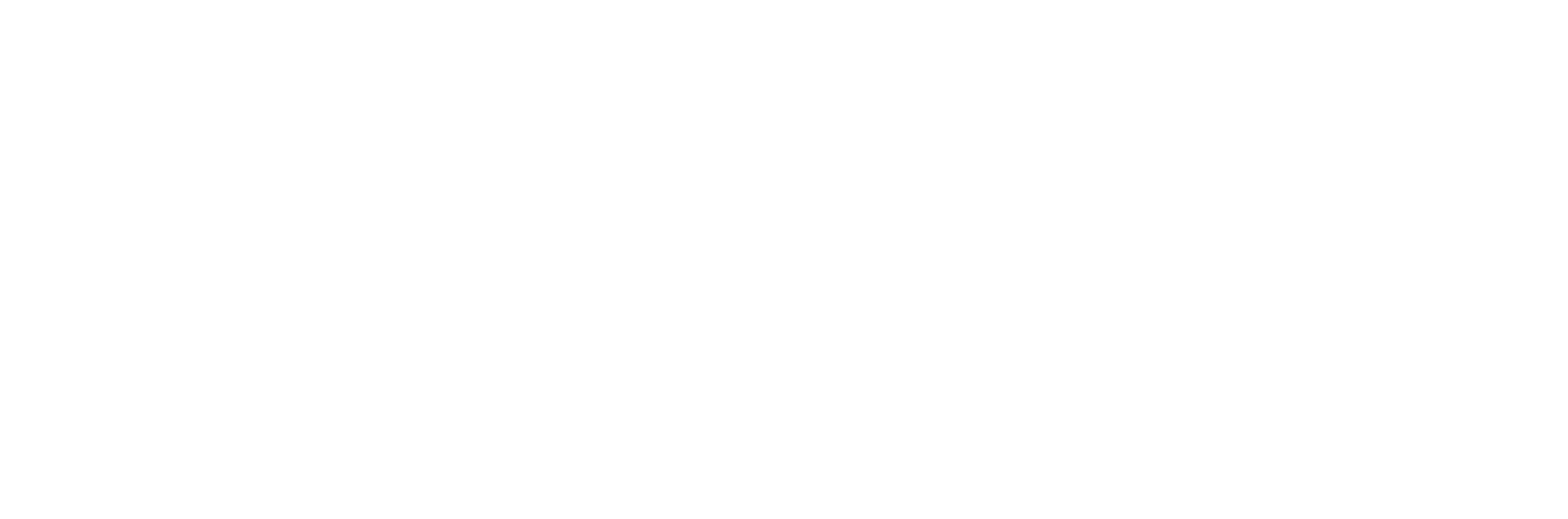
看法
文章详情
阔别已久的绿皮火车深夜嘶吼着、疾驰在广袤无垠的关中平原上。它像一条运输长龙,沿陇海线自西安出发,不久将会路过我的家乡武功,再不断往西,于陈仓关折向西北,最终于深夜时分驶入寂静的陇东大地,将明天的战士送到战场。

而回想今日凌晨,我还在广州飞往西安的万米高空上胡思乱想、记录些细碎。时间本是最珍贵的东西,但却由于交通工具的升级和生活节奏的提速,让人很难慢下来,作为律师更是难上加难。也正是此时此刻,虽然车厢已经熄灯,但耳旁不时传来亲切又嘈杂的低沉乡音与列车、铁轨迎合撞击奏起的慷慨交响乐,反倒让我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放松,让思绪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来写点法律文书之外的东西。
(一)
不经意间回头一算,从2019年9月2日迈入律所大门开始实习,至今从事律师事业已经五年多了。
而这五年,得益于入门师父的带领和指导,我所从事的律师业务大都与知识产权业务绑定了。这五年期间,自己在知识产权业务领域,不能说一事无成,也不能敢说有所作为,至少令人欣慰的是,有外地律师找我合作时,是通过裁判文书网上我所代理过的案子找过来的。
因此,趁本次知产周,和大家聊聊我的一些浅显想法和心路历程。
▸ 选择“知产”法律领域
说到当初为什么选择“知产”这个领域,其实不怕大家笑话。虽然我在法学院+法学系,满共读了六年法学专业,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却想从事传媒行业,在校期间,和一帮不务正业的伙伴喊过“因理想,为公义,求真相”的校园独立媒体口号。毕业后,也想着能够“以笔为杖”,通过新闻报道实现法条所难以表达的温度,这一系列的丰满理想或者认知偏差,最终导致在校期间我的法律专业基础知识不够扎实。
但毕业后,经过几次碰壁,发现传媒行业并非想得那么理想,甚至某天晚上喝了点小酒以后,还在深夜还给“呦呦鹿鸣”写了一封扯东扯西的信,吐槽了当下所面临的困惑与境遇。最终,经过再三抉择,我选择回归法学专业。那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好像我从小每逢考试就差点运气,我想考公大军中我应该是半路就会被淘汰的那一种,思来想去,好像能选的只剩下律师这一条路。

按照我在Icourt、智合实习时了解的律师行业知识,新一代的青年律师想脱颖而出,就得选择做专业律师。那么问题来了,我这样一个十分非正经法科生,上学期间,就民法学的一般,至于刑事、行政等领域更是陌生,若选择传统的民商行业,我自然竞争不过大部分正统法学院出身的法科生,就只能剑走偏锋,根据专业特长和兴趣踏入了知识产权业务的大门。
自此,我便开始了成为一名比较擅长知识产权业务律师的升级打怪之路。
▸ 适应“知产”律师身份
刚开始适应律师这个身份的时候,我着实有些吃力。诚然如师父所言“专业底子薄”的问题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刚开始,弄不清诉讼程序,写东西没有法律思维,有时候甚至连基本的法条都答不上来。当然,实习阶段除了本职工作吃力之外,还有身体上的疲劳,和物质上的贫瘠。
但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大概率就没有回头路了。这样的迷茫和无状态,持续了近半年才有所好转,而同时,慢热的自己也开始逐渐适应这个新的身份和生活节奏。

通过不断地打怪升级与在实务的海洋里沉沉浮浮,一转眼就熬到了2021年4月30日,当时我在去安康的高速上,收到了执业证下来的消息。终于,时隔一年八个月之后,我去掉了实习律师前面的实习两个字,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执业律师。
当时的心情复杂得难以描述,大体归为两类,一种是熬出来的释放,一种是被认可的喜悦。此后,就可以放手一搏了。
(二)
执业之后,我发现在西安,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少之又少。主要在于业务量太少,收费也不高。但凡有些高质量客户的高质量知产案件,再加上国知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在北京,因此,客户大都去北京找律师了。所以北上广知产律师的日常,是羡慕不来的。

藉藉无名的我自然不会属于那少之又少的部分,但也厚着脸皮声称,自己是擅长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至于案源方面,主诉案件,基本是北上广的同行和当地朋友介绍的案子。被诉方面,是当地朋友介绍和律所案源,主要是应对大品牌、公司起诉西安本地当事人的诉讼案件。
▸ 面对“知产”光怪陆离
其实知产业务和知产律师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光鲜亮丽,尤其在西部亦如此。和传统民商事业务代理流程的不同之处是,知产律师往往是从取证到诉讼一条龙服务,取证行为自然不能光明正大,但也不能鬼祟犯法,这就需要些技巧了。
比如曾经在兰州的街头,和公证处老师、城管满大街找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培训机构,而这个考研机构冒用了我们客户的字号;比如,我需要给被告的员工解释,一个陕西人,拿着河南大学本科毕业证,在毕业四年后,来山西太原报名一家非连锁的考研冲刺封闭班,声称要考山西大学的法律硕士,而我的目的只是想获取内部侵害著作权的培训资料;再比如,在东北某地的酒店里,架起三脚架和手机,对着电视盒子里的盗版节目一录就是十几个小时,而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个电视盒子中的内置软件方侵犯了我方电视节目的信网权……
此类的“离奇”行为每年都会发生好几起。只能说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对于律师而言,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自己的署名案例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据裁判文书网显示,这几年来,我也陆陆续续地代理了二三百个案件,这还不包括调解或撤诉的。而这当中,大量是批量知产诉讼维权案件,也夹杂着有不少个案。

▸ 相伴“知产”成长经历
批量知产诉讼维权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前几年社会各界因“潼关肉夹馍”“青花椒”等事件对该种维权行为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不可否认,批量知产诉讼维权有它的诟病,确实有相关权利人将此类诉讼成为谋利的工具。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该种行为对于净化市场环境,尤其是食品、餐饮、酒水等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起到的积极作用。
刚开始处理该类案件时,面对不知情商户的质疑和苦苦哀求,我还时常于心不忍,认为商户不知情,实在是可怜。当处理多了以后,尤其是在某次开完庭后,在法院停车场碰见刚在法庭上声泪俱下诉说自己生活艰辛的被告,在争取到较低的赔偿标准后,开着A8扬长而去的身影,那一刻,我承认我沉默了。此后,我会反复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的工作,即使我不处理,客户也会委托其他律师处理。
至于个案而言,大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逻辑比较简单。通常而言,只要权利人的基础稳固,同时对于侵权行为的取证没有程序瑕疵,则该案件问题胜诉的概率就比较大。但对于特殊的情况,如经营者主体变更、构成在先使用,不构成混淆可能性,或者专利权早已被公开等情形,则需要认真应对,仔细论证各种问题,否则很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在海里沉沉浮浮这几年,也是让我飞速成长的几年。感谢在我执业路上师父们的指导,让我有幸参与过周黑鸭、腾讯、饿了么、中粮、拼多多、高教社等知名品牌的主诉维权或应诉答辩。也让我有幸去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专业的知产法院或法庭开庭,不仅向对方律师取长补短,还能向法官学习缜密的裁判逻辑。
同时,可能是骨子里的记者特征:喜欢倾听和记录。在出差的路上我可以看见形形色色的人们,每到一个城市,我可以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可以和某个许久未联系的老友痛快地在他的地盘上喝顿酒,聊聊这许久未见的日子里,我们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
这也是一笔宝贵的人生经历。
(三)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做知产案件或知产律师有什么门槛?
我自认为是一个算不上聪明的人,但好在上帝没有把我的窗户关死。我还算是比较勤奋,也算是勤能补拙,才堪堪端上了律师这个职业赏的这碗饭。目前,和顶尖大律师和优秀的青年律师们还差的十万八千里,还尚在解决温饱问题的路上。
▸ 思考“知产”入行门槛
要是非得说有什么门槛?那排除“我爸是李刚”之类的天选律师,我认为所有的行业都是一样,热爱和勤奋是基础,要是能多点自知和真诚,凡事做到诸事有序,就足矣。当然我也没有达到,也是我对当下自己的要求。
之前闲下来胡思乱想的时候,总喜欢看《阿甘正传》,品那句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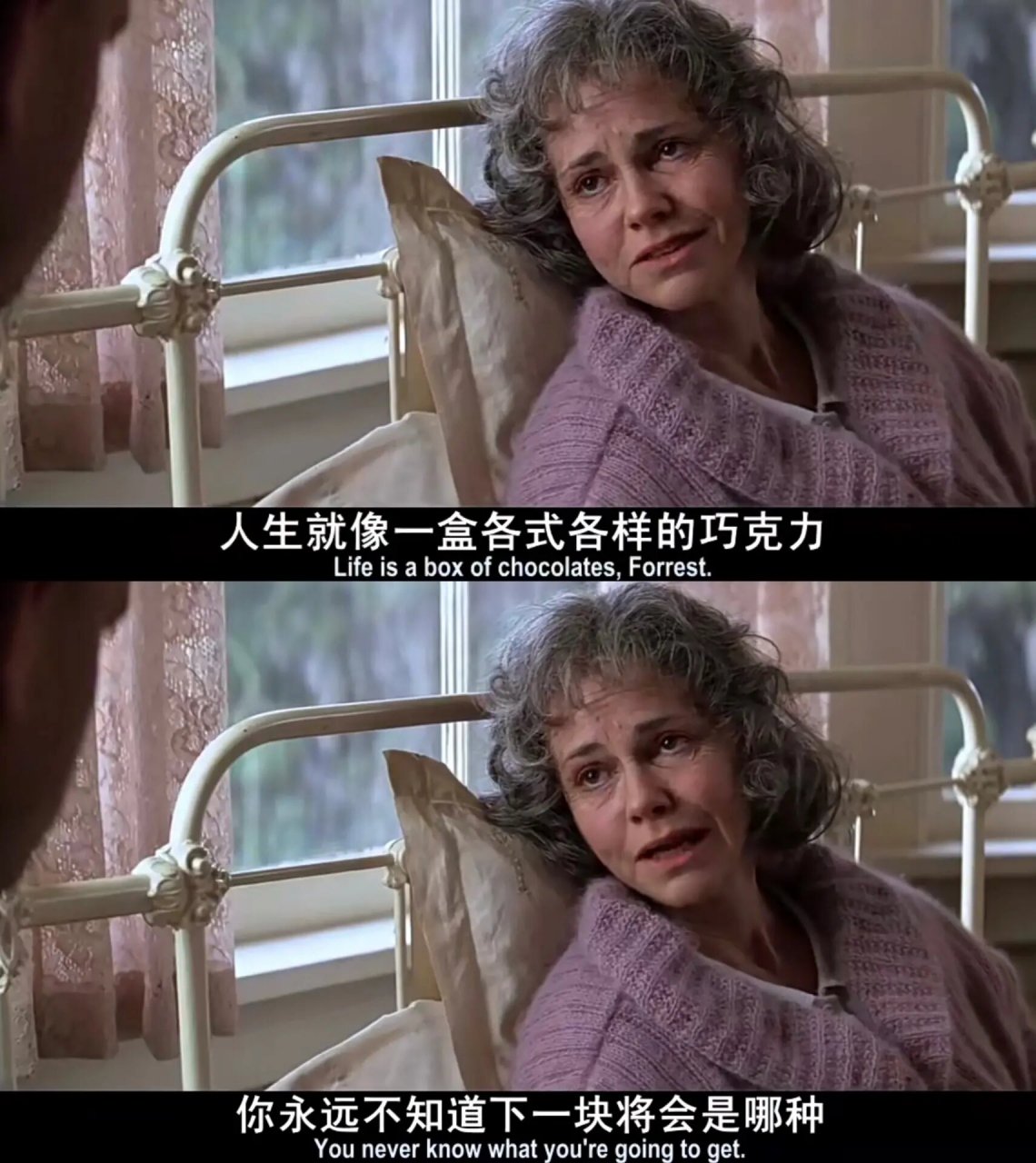
在2019年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公号里写道:我想知道属于我生活的这块巧克力,究竟是不是甜的?但很遗憾,我没有品出任何味道。我的内心仿佛有种声音告诉自己,克制以及理性,掌控好自己的情绪才是当下应该做的。遗憾的同时,也会感到抱歉,因为目前的我做不到那种克己状态。
在2021年的时候,我曾自嘲道:犹如初入越南战场时的士兵阿甘,可能是同届里混的最差的那一个,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否定无疑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容易击倒一个人的。但自己此时也没有太好的措施去缓解,毕竟是自己一步步把路走到这里的,怨不得别人。
2021年之后的很长时间,我好像始终在尝试不同的巧克力味道。现在,我想再次回应下:人生每一个周期阶段就像一块不同味道的巧克力,所处不同的阶段,生活就会沿着特定的轨道行走,每一步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使命。我们普通人无法选择,也无法逃避,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目前有且能做的,就像律师每一次应对开庭一样,全力以赴,问心无愧。
▸ 坚定“知产”未来征途
夜深了,火车穿过隧道时短暂的黑暗,像极了执业路上那些未可知的转折。车窗外的灯火零星亮起,思绪却愈发清晰——五年过去,我似乎才刚刚摸到知识产权领域的门槛,而门后的世界远比想象中辽阔。
未来的路该如何走?这个问题曾无数次在凌晨的案头浮现。
我始终记得,第一次站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庭上时,手心沁出的汗浸湿了案卷边角。对方律师从容引述判例,法官提问犀利如刀,那一刻的局促让我明白:知识产权律师的战场,早已不限于一纸诉状或几份证据。它需要更深的专业沉淀,更广的视野,以及对社会变迁的敏锐嗅觉。
是啊,五年前那个因“不够正统”而剑走偏锋的年轻人,如今仍在寻找答案。但至少,我已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处:在批量诉讼中坚守底线,在技术狂潮里保持清醒,在商业与公义间寻找支点。

未来的五年,或许我会继续在兰州街头“鬼鬼祟祟”取证,或站在最高法的法庭里激辩新规,又或者,带着一群同样“不务正业”的年轻人,为某个边缘创新者的权利奔走呼号。谁知道呢?
唯一确定的是:当法槌落下时,我仍会像初执业那天一样,心跳如鼓,热血难凉。
——陆续成文于4月22日深夜广州飞西安的飞机上、4月23日深夜西安往平凉的火车上